董卓的前半生:边荒之地的工具人
董卓仕途的起点,见于《吴书》记载,陇西太守召董卓为吏,职责是“监领盗贼”,具体的职务没有写。两汉有此职能的郡吏有门下督盗贼、门下贼曹、贼捕掾等。其中,门下督盗贼与门下贼曹分掌内外。门下督盗贼简称门下督或督盗贼,主要任务是侍从护卫太守;对地方盗贼的抓捕、审判,归属于门下贼曹。
贼捕掾在西汉宣帝时仍见京兆尹设置,至西汉末年,贼捕掾已沦落为与亭长并称的小吏。在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中,可见(劝农)贼捕掾的分部设置,即在长沙郡临湘县中,设东、南、西、北、左、右廷掾部,与游徼、亭长固定组合,即分区管理治安和劝农工作。
此职,至西晋时在县中仍有设置。
由此可知,董卓的第一份工作是陇西郡门下贼曹。之后,因为胡人出击抄掠,掳走人口,凉州刺史成就听说董卓能骑善射,就征辟董卓为州从事,正式职务为州兵马掾,或称州兵马从事。董卓上任后即率骑兵大破胡人,斩首俘虏数以千计。
注意,这里说的“胡”,不是入塞的羌人,用字也是“出钞”,可见是降服的属国胡人或是南匈奴胡人,能够惊动凉州刺史的劫掠,当然不会是百八十人的盗贼,而是大规模的入侵。从《后汉书·南匈奴列传》的记载来看,董卓可能遭遇的匈奴、诸胡成规模寇掠凉州有三次:
其一是永和五年(140年)秋,南匈奴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,东引乌桓,西收羌人、诸胡数万人,寇掠并、凉、幽、冀四州;其二是永寿元年(155年),匈奴左薁鞮台耆、且渠伯德等复叛,寇钞美稷、安定,被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败;其三是延熹元年(158年),南单于诸部一齐反叛,与乌桓、鲜卑联合寇掠边境九郡,北中郎将张奂击破之,南匈奴降服。
已知董卓于延熹九年(166年)至永康元年(167年)间为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之军司马,参与了平定凉州叛羌之战。则永和五年之战太过久远,而永寿元年(155年)之战范围不大,可知,董卓被凉州刺史成就任命为州兵马从事应在延熹元年(158年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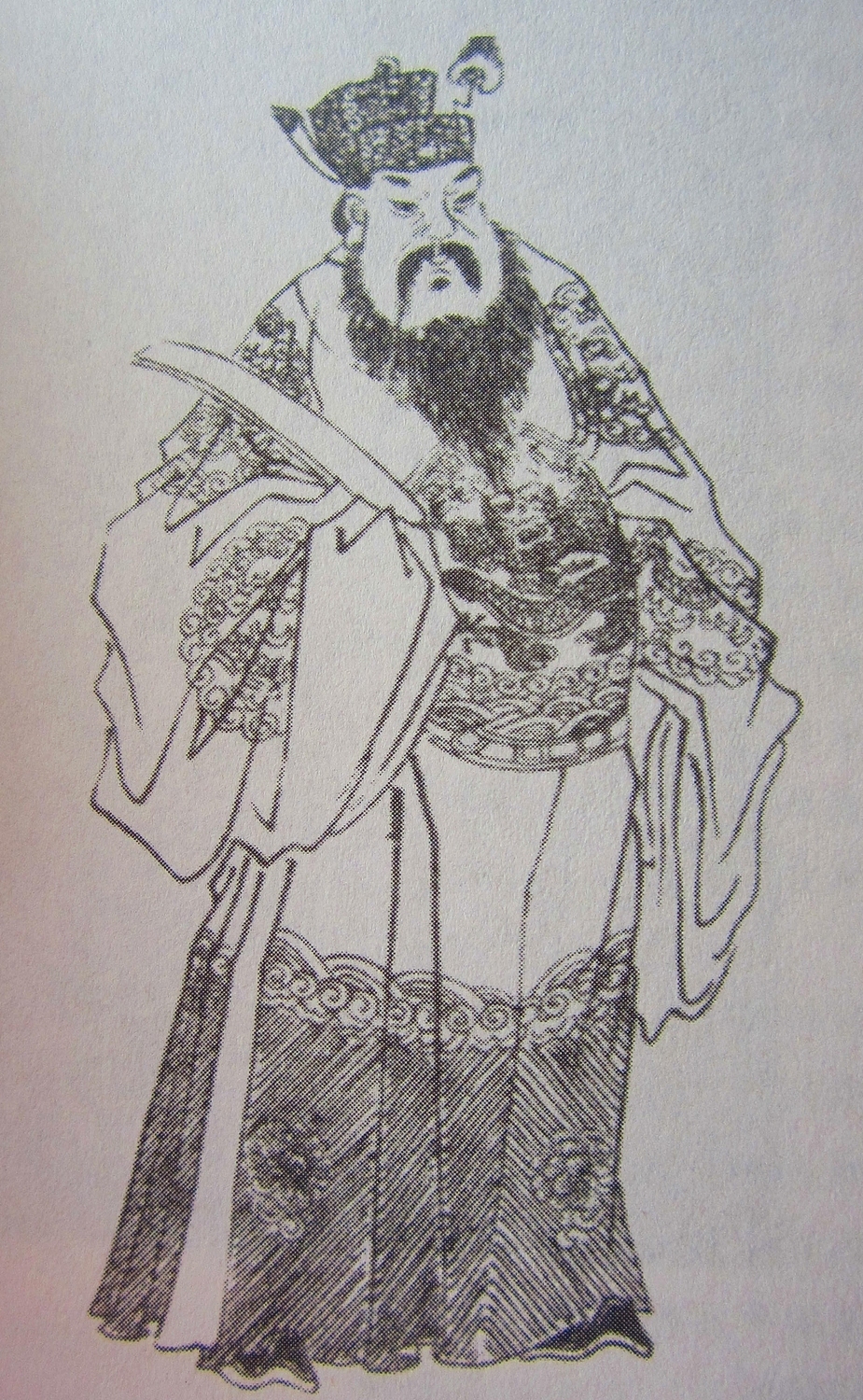
董卓
按照《吴书》的说法,在董卓大胜胡人之后,就被并州刺史段颎推荐到公府,司徒袁隗辟其为掾。在时间上有很大的破绽。
段颎任并州刺史在汉桓帝延熹四年(161年)到延熹六年(163年)之间。而袁隗一生中两任司徒,第一次在汉灵帝熹平元年(172年),次年被罢;第二次在汉灵帝光和五年(182年),中平二年(185年)免官。很明显,这两件事不可能有关联。
所以,段颎推荐在先,董卓入袁隗司徒府在后,是两件事。而段颎任并州刺史期间,朝廷的三公有种暠、许栩、刘宠、刘矩、杨秉等五人,其中,种暠自延熹四年二月至延熹六年二月任司徒,死在任上;许栩于延熹六年三月继任司徒;刘宠于延熹四年九月为司空,延熹六年十一月免;刘矩于延熹四年四月任太尉,延熹五年(162年)十一月免,杨秉继任。
在五人之中,与凉州关系最紧密的就是种暠,他任凉州刺史当升迁时,当地百姓不放他离开,纷纷入朝叩阙请求种暠留任。梁太后为之啧啧称奇,没听说过刺史得民心到此等地步,于是破例允许他留任一年,再升他为凉州汉阳太守。羌胡百姓将他送到汉阳郡界,一路上反复道谢,以至于行程千里不得乘马车。在种暠死讯传出后,并州、凉州的百姓都自发为他举行哀悼仪式,南匈奴更是举国伤痛惋惜,单于每次入朝洛阳时,望见种暠的坟墓,都哭泣祭祀。
很明显,种暠是朝廷重臣之中,少有的对凉州、并州边地没有成见的人物。而且,在董卓进京的途中,何进派出阻止董卓的使者,正是种暠的孙子,种劭。当时,种劭以劳军的名义,要求董卓退兵,董卓怀疑有变,让士兵持兵器威胁种劭。种劭大怒,口称诏书大声呵斥,兵士尽皆披靡,上前质问责难董卓,董卓说不出话来,只好退兵夕阳亭。可见,董卓对种劭的处置,绝对是心有忌惮,一方面是顾忌种氏在凉州人心中的余泽;另一方面,应该也与他曾为种暠故吏有关系。
注意,故吏并不是从任职算起,受到举荐就可以视为故吏。比如,司空袁逢在党禁解除后,举荀爽为“有道”,荀爽没有应举,可待到袁逢死后,荀爽为其服丧三年,就是以故吏的身份为主服丧,“当世往往化以为俗”。
而从董卓的宦历来看,他受段颎举荐入公府,极有可能赶上了种暠病危,故而,没能受辟为掾吏。在种暠死后,董卓失去了依靠,只能以六郡良家子任羽林郎,当时,虽然还是汉桓帝执政,没有西园卖官,可汉桓帝延熹四年(161年),已经开卖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、五大夫。可知董卓的羽林郎大概率是出钱买的。
这个情况,也恰好可以和张奂与董卓交往中的一件事对上。据《后汉书·张奂传》记载,在张奂成为将帅之后,董卓仰慕他,让大哥董擢带着一百匹缣给张奂送礼,结果,张奂厌恶董卓为人,拒绝不受。此事未记录时间,既然张奂成为“将帅”,则应该在他出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,即延熹九年(166年)秋之后。
尽管张奂在此之前,曾于永寿元年(155年)至延熹二年(159年)之间任使匈奴中郎将,于延熹六年(163年)后任度辽将军,可以称“将”,却绝对算不上“帅”,因为这两个职位都是监护南匈奴的,并非出征统帅。
直至延熹九年秋,张奂拜护匈奴中郎将,以九卿秩督幽、并、凉三州及度辽、乌桓二营,兼察刺史、二千石能否,这才是真正的元帅之任。而前文已述及董卓任凉州兵马从事在延熹元年(158年);受段颎推荐入公府,应该在延熹四年到延熹六年之间,时间上都不匹配。
而且,董卓“慕”张奂,说明两人没见过面,距离也远,才请兄长代为致礼,再考虑到张奂“恶”董卓为人,说明他对董卓名声也有耳闻。而董卓早年并无劣迹,唯一可能的坏名声就是花钱买羽林郎,让洁身自好的张奂感到厌恶。可是,退还财物不接受,并不代表不用董卓,恰恰相反,由于朝廷话语权的问题,凉州人才堪将校的人物并不多见,董卓的主动结交,反倒让张奂认识了董卓,于是命他担任军司马,在永康元年(167年)与司马尹端一起攻打汉阳郡的叛羌,“大破之,斩其酋豪,首虏万余人”。
可为什么凉州人的话语权小呢?
要知道,东汉末年有“凉州三明”,即皇甫规(字威明),张奂(字然明),段颎(字纪明),在并州和凉州,对羌人、氐人、南匈奴、屠各胡等各部或征战,或安抚,维持了北部边疆的稳定。后来还有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,也是一代名将。
根本原因在于,凉州地当边境,羌汉杂处,事烦责任重,在东汉的政治版图上可有可无,前途广大的清贵士人都不爱去此地做官。尽管同为边州的并州、幽州、交州也差不多,可是,凉州尤其不受重视,甚至在朝廷上曾有过两次“弃凉州”之议。
早在汉安帝永初四年(110年),羌人叛乱蔓延并、凉二州,大将军邓骘提议放弃凉州,内迁郡县,集中力量解决北方问题。陈国人虞诩苦劝太尉李修才得以阻止。待到汉灵帝中平四年(187年),由于边章、韩遂反叛,战事不休,后勤负担太重,司徒崔烈再次提出弃凉州的意见。汉灵帝有意接受,下诏公卿百官会议,遭到北地人傅燮的厉声斥责,要求斩杀崔烈。最终,灵帝驳回了崔烈的提议。
可见,相对于并州这个洛阳的北边屏障,凉州在东汉中枢的眼中就是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两次“弃凉州”的主要考虑都是战乱不断,后勤压力太大,不如扔掉,让朝廷财政喘口气;两次阻止“弃凉州”的说辞也都一模一样,因为当地民风悍勇,如果被胡虏或是豪杰占据,成为东进的基地,东汉王朝很有可能被灭。
无论是弃还是留,都没有考虑凉州这块土地的价值,以及当地百姓的福祉,相当悲哀。不过,虞诩的建议终究有利于凉州人,太尉李修被他说服后,集合四府商议,确定了一项制度,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等四府,要征辟凉州豪杰为掾属,并任命当地出身的刺史、太守、县令、县丞、县尉等官员子弟为郎,“以安慰之”。
董卓受段颎推荐入公府,应该就是受益于这一政策,而他的经历也表明了,这一政策的截止时间,应该就是延熹六年(163年)种暠去世。之后朝中再也没有对凉州有感情、有了解的三公强力推动该制度执行,这就导致了凉州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声音越来越弱。直到汉灵帝即位,董卓、皇甫嵩、盖勋、傅燮等人才得到了重视。
而凉州的大人物们,又要分一分类。
皇甫规,父亲皇甫旗为扶风都尉,祖父皇甫棱为度辽将军;皇甫嵩,父亲皇甫节为雁门太守;张奂,父亲张惇为汉阳太守;盖勋,家世二千石,祖父盖彪位列九卿,为大司农,父亲盖思齐为安定属国都尉。这是一类,显宦之后。
另一类,是读书有道。比如傅燮,史书无父祖阀阅,却说他“少师事太尉刘宽,再举孝廉”;段颎,父祖也无可称道者,但是“长乃折节好古学。初举孝廉”。其实,前一类的显宦之后,也一样走过察举的程序,皇甫规“举贤良方正”、皇甫嵩“举孝廉、茂才”、张奂“举贤良”、盖勋“举孝廉”。
董卓呢?父亲是个县尉。也就是说,他的家世勉强可以享受永初四年(110年)确定的对凉州官员子弟的优待,毕竟县尉也是长吏,只是是最低档。但是别忘了,董卓是次子,所以,如果他不钻营,求段颎推荐,入公府这种好事肯定没他的份儿。
至于举孝廉,在东汉末年一样要看家世、名声、师承,学问倒在其次。董卓在游侠归来后,还要下田种地,说明他的家族并不富裕,经济条件的改善还是靠他收来的一千多头杂畜,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“暴发户”。这种家世,根本摸不到郡内著姓的边,故此,董卓在社会阶层上,不但比皇甫规等人低,比段颎、傅燮还要低。
永初四年的安慰政策,主要优待的是现任官员子弟,尊长为官,则子弟可以入朝,再外派为官,就在凉州形成了一个固化的世家群体,他们在经学传统和师承圈子上,无法和内郡比拟,却拥有一条汉王朝预留的入仕捷径,那就是“关西出将,关东出相”。这也是虞诩谏阻“弃凉州”的理由之一,“观其习兵壮勇,实过余州”,凉州民风彪悍,“数与羌战,妇女犹戴戟操矛,挟弓负矢”,因为能打,所以可以参军打仗。
问题是,东汉中央常备武力多出自汉光武帝的元从后人。所谓将帅,只是战争爆发时临时任命的统兵官;所谓将士,要么是主将的家兵转为部曲,要么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义从,战事结束就要交还兵权,解散大军。所以,当大规模战争结束后,凉州出身的将校,往往会被派往护羌、度辽等边疆营部,或在内郡辗转任太守。整个东汉传八世共十四帝,享国一百九十五年,第一位凉州籍三公是靠着党附宦官上台的段颎,第二位就是董卓了,他也是东汉历史上唯一一位相国、唯一一位太师。
可段、董二人实为异数,并不具有代表性,凉州人绝大多数时候根本没有话语权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缺少三公五府的提拔,凉州察举的人才只能沉沦下僚,奋斗一生也主持不了官吏选举,久而久之,只有在打仗时会想起凉州将校,太平盛世则弃若敝屣。
了解了这些,应该就能理解,董卓在东汉王朝的制度背景下,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的艰难。家乡是负担,家世是负担,读书是负担,哪怕是武勋,加上他的籍贯,也是负担,可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负重前行,最终登顶的呢?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诀吗?
董卓凭什么不像一个凉州人?
凉州其实是个好地方,它地处丝绸之路要冲,西连西域,东接关中,商贸极其发达。据《后汉书·孔奋传》记载:“时天下扰乱,唯河西独安,而姑臧称为富邑,通货羌胡,市日四合,每居县者,不盈数月辄致丰积。”说的就是汉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情景,姑臧县是武威郡的治所,市场达到了一日四合,什么意思呢?
古代市场一日三合,早上叫朝市,中午叫大市,傍晚叫夕市,增加一合,就是夜市了,这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被允许。偶尔出现的,比如桓谭《新论》中提到过,右扶风的漆县邠亭,当地人习俗是约定好时间,夜间赶集贸易,如果不遵守约定时间,会遭遇严重的灾祸。这个夜市,在当时属于国家级的稀罕事,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“邠”时,也提到了这个特殊的乡俗。由此可见,武威郡姑臧县商业活动的繁盛,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原人的想象。因此,在姑臧做县令,只要几个月就能贪得盆满钵满。
这些财富,一部分得益于丝绸之路上往来贸易的粟特商人。早在东汉初年,耿舒讥讽马援平五溪蛮的大军迟缓时,就打过比方,“伏波类西域贾胡,到一处辄止”。可见,时人已经对贸易途中隔一段就建立聚落的中亚粟特人做派非常熟悉。这些聚落在东汉王朝设于西域的屯田、驻军庇护下,连点成线,构成了一条稳固的贸易路线,其盛况在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中就有描述:“商胡贩客,日款于塞下。”
此外,混居于凉州的羌人,也多有良马和金银。比如张奂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期间,有效地隔绝了匈奴与东羌势力,东羌豪帅纷纷向他送礼示好,一次性赠马二十匹,先零酋长更是给了金鐻八枚。鐻也称鐻鍝,在甘肃省博物馆中有实物,高四厘米以上,是汉代少数民族佩戴的耳坠,可见羌人手中黄金之多。张奂先收下礼物,后召集羌人,以酒酹地,说:“使马如羊,不以入厩;使金如粟,不以入怀。”意思是,就算马像羊一样多,黄金像粟米一样多,我也不要一分一毫。
之后,张奂又把礼物送还原主。按照《后汉书》的说法是,羌人生性贪财,却又崇敬清廉的官吏,之前有八任属国都尉都是贪财好货之徒,羌人被盘剥得很痛苦,张奂能够廉洁自守,立刻受到羌人的推崇。
这个例子,充分说明了凉州当地羌人的富裕。连续八位属国都尉都是贪婪之徒,可见当地的黄金、良马何其之多,引人贪欲,也充分说明了东汉中后期羌乱不息的根本原因。
东汉朝廷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要钱、不要粮,只要他们当兵从征,看起来负担很轻。可地方官往往贪暴,他们的私下盘剥往往施加在羌人豪帅的头上,这些人不但有黄金,还有强兵、良马,地方官要价超过他们的心理价位时,必然会举兵造反。所以,贪婪的地方官压榨羌人财物的结果只有一个,那就是叛乱。
那么,贪官们能做到什么地步呢?
皇甫规的经历可以给我们答案。汉桓帝延熹四年(161年),五十九岁的皇甫规主动请求领兵讨平叛羌,三公共举他为中郎将,持节监关西兵。皇甫规到凉州后,只打了一仗,东羌各部就自动请降。待中原与凉州的联系恢复后,皇甫规就上书弹劾了贪暴的安定太守孙俊,肆意杀害已降羌人的安定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禀,以及倚仗朝中权贵,横行不法的凉州刺史郭闳、汉阳太守赵熹。待皇甫规处理完这些贪官酷吏,羌人叛军竟然立刻有十几万口投降。
羌乱看似平定了,可是,“凡此五臣,支党半国,其余墨绶,下至小吏,所连及者,复有百余”。这里面,支党半国不是说东汉王朝的国,而是凉州辖区内的州府属吏和郡国太守,有一半是上述五人党羽,而墨绶一般指县令,自此以下,还能牵连百余人。可见,到了汉桓帝时代,凉州官场已是塌方式腐败,无怪乎羌人、氐人、湟中义从胡此起彼伏地造反。
在朝野上下利益关联方的共同发力之下,皇甫规被弹劾用财物贿赂叛羌投降,是欺骗朝廷。结果,皇甫规虽未因此入罪,却因为拒绝宦官的索贿,有功不赏,被以“余寇不绝”的罪名处理,直到朝廷大赦,才得以归家。这个遭遇,与同样主张招抚羌人的张奂差不多。按照皇甫规上书中的解释,他自己平定羌人叛乱,只花费了一千万钱安置叛羌就恢复了安定,大约为朝廷节省了一亿钱的军费。不过,他们两个人的招抚策略,在朝廷眼里属于劳而无功,因为羌胡往往降而复叛。
段颎对此的态度是坚决镇压加屠杀。“凡百八十战,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,获牛马羊骡驴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,费用四十四亿,军士死者四百余人。”看似一劳永逸,四十四亿的花费也远少于永初年间十四年里二百四十亿、永和年间七年里八十余亿的军费支出,可是,朝廷派来的刺史、太守贪暴的问题无法根除,凉州的叛乱也将永无止息。
董卓的人生奇迹,就发生在这持续叛乱的背景之下。
汉桓帝永康元年(167年)冬,董卓跟随张奂讨伐叛羌,与尹端同为军司马,大破汉阳郡叛羌,斩首、俘虏万余人,凉、并、幽三州平定。论功行赏的时候,张奂的功劳本该封侯,可因为“不事宦官”,只赐钱二十万,任命一名家人为郎,张奂推辞不受,请求朝廷允许他迁徙户籍到弘农。而董卓却得拜郎中,赐缣九千匹。缣是一种平纹丝织品,长四丈、宽二尺二寸为一匹,按照敦煌汉简中的记录,东汉章帝时凉州敦煌郡一匹缣的价格是六百一十八钱。另据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汉简记录,东汉和帝、安帝早期的荆州长沙郡临湘县,一匹缣价格八百二十钱;另有单买五尺缣值钱一百七十五,则一匹价格为一千四百钱,不知什么缘故差价如此之大。就按最少的算,六百一十八钱一匹,九千匹缣总值五百五十六万两千钱,是领军主将张奂所获赏赐的近二十八倍。
董卓在受赏之后,把所有赐缣都分给了部下,一点儿没留,还说了一句经典的话:“为者则己,有者则士。”意思是立功受赏的是自己,创造功勋的却是兵士,可见他也有仗义疏财的性格特质和相当强的底层共情意识,理解募兵义从的诉求主要是财物的赏赐。
只看这个结果,张奂赏薄,董卓得到厚赏,二人似乎是走了两条路,一个“不事宦官”,另一个必然谄谀宦官了。其实不然。就像董卓虽然受过段颎的举荐,却和段颎不是一路人一样。董卓的仕途独辟蹊径,拿到军功后,非但没有跟随段颎平定东、西羌,参加波澜壮阔的平羌战争,反而转去做了文官。
建宁元年(168年),张奂振旅还朝,董卓受任郎中。前文中讲过规矩,不满一年称郎中,满一年称侍郎,所以,董卓任郎中不到一年,就升迁为并州雁门郡广武县令。这个职务,前文也讲过,属于大县县令,是郎官中的高选,意味着董卓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之后,终于进入了东汉官场的正常升迁路线。中间的财物贿赂代价我们不得而知,只看斩首数量,在凉州从事任上有千余级,平叛羌又有万余级,加起来一万一千多头颅,才换来了这么一个正常升迁的入场券。
此后,他又由广武县令升任益州蜀郡北部都尉,辖区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、汶川、理县一带,主要管理的是大批内迁的蜀地羌人和氐人等少数民族。之后,转任西域戊己校尉,治所在高昌,地点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市境内,职责是负责镇守西域。之后,因犯罪被免职。
董卓上述的宦历,没有时间的记录,却可以参考他入司徒袁隗府中为掾的时间。前文中提及,袁隗两任司徒,第一次在汉灵帝熹平元年(172年),次年被罢;第二次在汉灵帝光和五年(182年),中平二年(185年)免官。可以确定的是,董卓中平元年(184年)任东中郎将,受命对阵黄巾,之前曾任并州刺史、河东太守。这里面河东是司隶校尉部所辖,是东汉王畿的“三河”(河东、河内、河南)重镇,人口极多,一直是太守中的重职,士大夫不可能在此职未免官的情况下,入三公府为掾属。
所以,董卓入袁隗府中时间应该在袁隗第一次任司徒时,即熹平元年、熹平二年(173年),也是他坐事免西域戊己校尉之职后。这里要讲述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,就是“故吏”概念。在东汉,“故吏”往往指曾经的属官,但在行政制度层面,“故吏”这个词还有一重含义,指代曾经的官吏,比如因疾病、服丧,或是罪责免职的官吏,只要没有被“废”或“禁锢”,都可以重新入仕,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任官资格,不需要从头再来,反倒会有快捷通道。
董卓之前任职的蜀郡北部都尉和西域戊己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官,他被袁隗征辟为司徒掾后,不需要再任郎官,而是直接由尚书台选举,授拜秩六百石的并州刺史,政绩卓著才能升迁为大郡太守。所以,董卓在并州刺史任上应该表现不错,这才升秩为二千石的河东太守。
也就是说,董卓可能在并州刺史、河东太守任上干了十一年(173年至184年),之前的几个地方职务,包括免职在家的时间,约有三四年(169年至172年或173年)。从建宁二年(169年)开始,到中平元年(184年),董卓就没担任过出征军职,这个时间长达十五年。当然,从他的自述来看,这期间他也有领兵,所谓“掌戎十年”,即从光和二年(179年)到中平六年(189年),按光和二年有鲜卑入寇并州,应该是并州刺史董卓领州兵、部曲抵御。
不过,无论如何,董卓十五年间所任职衔,除了西域戊己校尉,其余与凉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凉州高官惯例担任的本州属郡太守,以及镇压羌人的属国都尉、护羌校尉,镇压南匈奴的度辽将军、使匈奴中郎将等职位,他一个都没沾,而比他早出名的“凉州三明”几乎一辈子在这些职务上辗转。
董卓经历的反面,就是段颎统帅护羌营时担任军司马的田晏和夏育。田、夏二人一直跟随段颎平羌作战,手上沾满了凉州羌人的鲜血,可辉煌的战功给他们换来的还是戍边的武职。比如,熹平三年(174年)夏育任北地太守,北地郡属凉州,是典型的边州边郡,太守必须习武事,能领兵,只不过任务变成了与更强悍的鲜卑人作战,之后他上书请求攻打匈奴,又从太守调任了护乌桓校尉;田晏任护羌校尉,熹平六年(177年)时,田晏因为犯法当受刑被赦免,就想立功报效,于是贿赂中常侍王甫,请求北击鲜卑,改任破鲜卑中郎将,从没仗打的凉州边境转到了有仗打的并州、幽州边境。
待到熹平六年,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与使匈奴中郎将臧旻、护乌桓校尉夏育,分别自云中、雁门、高柳三路出击鲜卑檀石槐,遭遇大败,每路出动的一万骑兵,各自只带回了几十人,死者达七八成,一次性葬送了并州、幽州北部边疆的三万精兵。
这次惨败对董卓的影响也很大,据他中平六年(189年)的自述,“天恩误加,掌戎十年”,则他自光和二年(179年)开始领兵,原因应该就是并州方向的营兵葬送殆尽,只能由并州刺史招募义从,阻击鲜卑的入侵。当年十二月,鲜卑即寇掠幽州、并州,此后连年入侵,直至光和五年(182年)冬才没有记录。董卓或于次年,即光和六年(183年),因边功升任河东太守。
至于出击惨败的三位凉州主将,可没有好下场,全数下狱,出钱才赎为庶人。直到中平元年(184年),被重新启用为护羌校尉的夏育,被叛羌围困在右扶风畜官,汉阳长史盖勋率军救援兵败,此后,夏育的生死不知。
这就是凉州将领的宿命,更高级的帅才,也不见得命运更好。汉桓帝延熹四年(161年)冬,平定羌乱,功当封侯的皇甫规,遭到了中常侍徐璜、左悺的敲诈,他们多次派出宾客询问皇甫规平乱的细节,皇甫规一直没有搭理。徐璜等人愤怒,以之前的案子陷害他入狱。皇甫规的属吏想要挪用公款为他求情,遭到他的坚决拒绝。之后,朝廷论罪皇甫规为“余寇不绝”,判处“输左校”,后来赶上大赦才得以归家。
张奂的遭遇,前文已经说了,不再赘述。段颎则是一直党附宦官,甘为其爪牙,待到阳球诛杀宦官时,也与王甫父子一同入狱,以自杀告终。哪怕是后来的皇甫嵩,在平定黄巾之后,功震天下,中常侍张让也敢于私下向他要五千万钱的贿赂,皇甫嵩不给,被弹劾连战无功,花费太多,收了其左车骑将军的印绶,削户六千,改封二千户的都乡侯。另一位跟随皇甫嵩的凉州人傅燮,任护军司马,斩杀了黄巾三帅(卜巳、张伯、梁仲宁),功勋实为诸将第一,理当封侯,结果因为中常侍赵忠厌恶他对宦官的态度,进了谗言,还是汉灵帝本人赏识傅燮,才得以不加罪,但也没得到封赏。
凉州将帅非但不再是朝廷安慰的对象,反而成了宦官们敲诈的目标。
在此背景下,董卓远离战场十五年,反而快速升迁,无疑让他成了凉州豪杰中的异数,可是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?
要解答这个问题,就得回顾董卓仕途的关键转折点,到底在何时、何地,与何人有关。其实,时间点很清晰,就是建宁元年(168年),董卓因功授郎中;熹平元年(172年)或熹平二年(173年),董卓受辟为司徒掾。
值得注意的是,建宁元年正是汉灵帝登基之年;而熹平元年则是窦太后去世之年,自此年之后,一个重要人物登上了东汉的政治舞台——孝仁皇后董氏,用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中的话说,是“及窦太后崩,始与朝政”,也就意味着,董后开始干预朝政了。
值得注意的是,建宁二年(169年),汉灵帝即迎董后进京,并征召董后之兄董宠。为母上尊号的同时,汉灵帝拜舅舅董宠为执金吾,“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,下狱死”。也就是说,汉灵帝提拔董氏外戚,遭到了未知力量的狙击,甚至到了杀人的地步。
而在《后汉书·董卓列传》里明确提到,董卓进京后,之所以要废少帝立献帝,原因是:“卓以王为贤,且为董太后所养,卓自以与太后同族,有废立意。”董卓与董太后的关系,未见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载,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。前文中介绍过,同族为五服之内,同宗为五服之外。董卓是董后五服的亲族,而董后是“蕃后”出身,原本只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夫人,从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中说汉灵帝“本侯家,宿贫”的情况来看,董后的母家应该也不是巨富世家,故而人才有限,想提拔外戚也没人可用。
故此,哪怕陇西郡与河间国老家相隔万里,可能早就断了来往,同族的董卓说起来还是比旁人更亲,所以会重点培养。这也恰恰可以解释,董卓在进京之后对“故主”袁隗不尊重的原因,俩人本来就没有君臣知遇,只是袁隗投董后所好,借花献佛的手段。董卓自然不会感激袁隗的政治投机。
考虑到汉灵帝登基时只有十二岁,时人早婚育,董后的年龄也不会很大,董氏下一代的人才只有董重受任为五官中郎将。董宠被杀之后,董氏一族缺少实力支撑,董卓又以武勋知名,正是支持董氏地位的首选。
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董后之侄董承才在董卓军中,为中郎将牛辅部曲。而董卓的亲弟弟董旻,也得以在洛阳担任奉车都尉。奉车都尉原本是为皇帝驾车的角色,但多由贵戚出任,如霍去病之子霍山、霍去病之弟霍光、汉光武帝之女婿窦固都曾任此职,与驸马都尉、骑都尉合称为“三都尉”。至西晋时,“晋武帝亦以皇室、外戚为三都尉而奉朝请焉”。
可见,董卓家族实为董后外戚。了解了这一背景,再看他对汉灵帝的痛骂,以及对何氏一族的残酷,就可以理解了。他很可能与董后同辈,汉灵帝于他实为亲族晚辈,眼看着天下纷乱,实在是恨铁不成钢。至于何太后,罪名是“踧迫永乐宫,至令忧死,逆妇姑之礼”。东汉时称儿媳为子妇,称婆母为姑,可见,董卓是用欺压婆婆的不孝大罪来处置何太后,又对何苗开棺戮尸,斩杀何后、何苗之母舞阳君,尸体扔在乡间不得收敛,无疑是在用最酷烈的手段为董后复仇。
所以,董卓的仕宦经历之所以与其他凉州豪杰不同,根子就在于,他朝中有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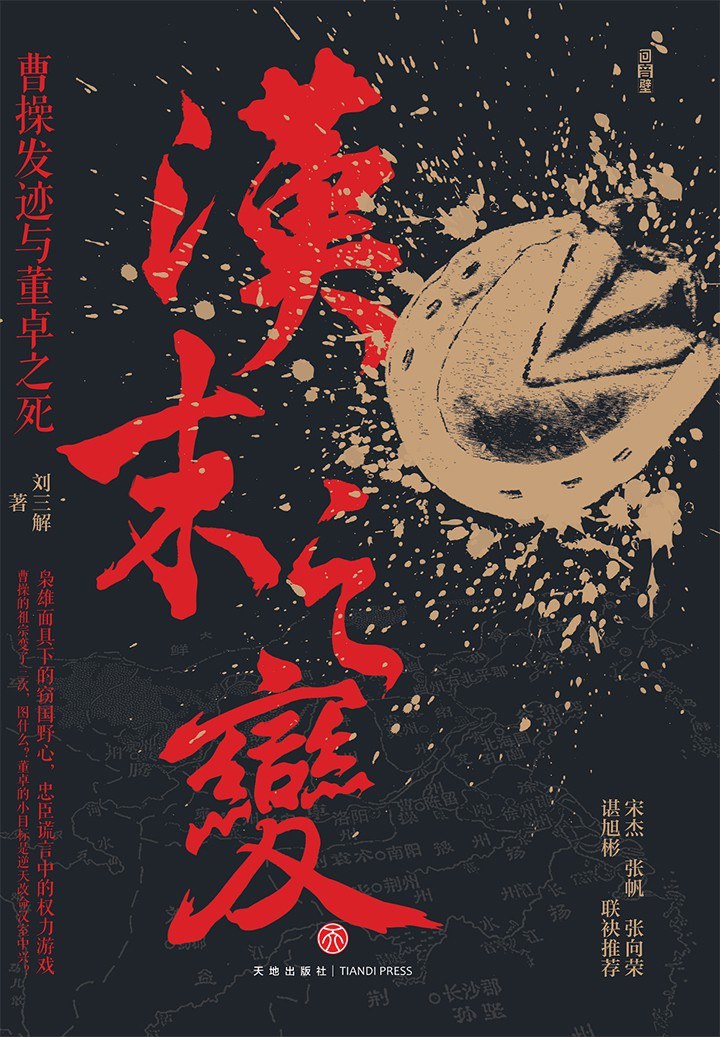
本文节选自《汉末之变: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》(刘三解 著,天地出版社 | 天喜文化,2025年3月版)